--作者:林向北
第四部分 在“左”祸横行的年代
内容简介
1949年12月30号,解放军进驻重庆城。我仅用两天的时间成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了来自渣滓洞、白公馆和其他监狱里出来的难友及其家属。一位老战友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分的说:“小林你还活着啊!”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脱险同志都分别做了安排,诗伯和梅侠到市妇联,宁君到市委宣传部,亚彬到公安局,我到市委招待所,不久又调到市委统战部,随后去巴县和南川参加土改工作。
“三反运动”开始之前,诗伯就以“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等罪名,被强行“劝退出党”。接着我成了“用大卡车偷运金条”的大老虎,审查两月,结果不了了之,调到二区委(即江北区委)作办公室主任。
1954年夏天,我作为“优秀干部”,奉调到地处长寿县的狮子滩水电工程局,在这个“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朵鲜花”绽开的地方,先后在供应处和局办公室负责,为电站提前一年发电做出了贡献。为了想为家乡多做贡献,我拒绝上调水电部,谁知大祸来临,我这个功臣竟成罪人,被打成了“右派”,进入了我人生最为痛苦的时期。
1958年,我被转送到紫坪铺水电工地上劳动改造,竟然当上工区经理,正准备给我“摘帽”时,上面指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美梦破碎了,又被打到煤窑去劳动改造。
1960年,诗伯病逝,我去重庆奔丧,居然不准见她最后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
1962年,我奉调到省文联,同宁君一道整理诗伯的回忆录《华蓥风暴》,初稿刚成,“文革”开始,《华蓥风暴》成了“黑书”,文联主席沙汀成了“炮制者”,我也成了“牛鬼蛇神”。书稿的出版成了泡影。
1995年,《“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上天终于洗刷了诗伯的冤情,还我们以清白。
第二十章(一)
欲罢不能
比起解放前来,解放后的这段历史实在是不大好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我离休,整整32年。这期间,我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先是凭着对党对革命的一片忠心去帮着整人,没想到很快自己就成了“专政对象”,其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实在是一言难尽。那二十多年,正是我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时候,8000多个日日夜夜啊,却眼睁睁看着它们流失了。常言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它在我心中刻下了苦涩的烙印,令我至今心有余悸,有打油诗可以作证:
熬过了艰难岁月,迎来新的生活,原以为从此平安过,谁知长夜难眠噩梦多。是真是假难分辨,是好是坏各说各,是人是鬼看不清,是生是死任宰割,年年斗呀天天斗,斗得你死我要活,婆婆多啊庙门多,拜了这个拜那个,说了假话心有愧,说了真话跑不脱。何必惹事生是非,只好就此把笔搁。
可是历史总是要被记录的,担负起这项责任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害人的;二是被害的。而被害的人中,绝大多数已不在人间,有幸活到今天的,不是老弱多病就是心灰意冷,大都不愿自找麻烦。好在我们中间,还有像季羡林、韦君宜、马识途这样的人,他们虽说也都是垂垂老者,却出于对历史的责任,用血泪写成了诸如《牛棚杂记》《思痛录》《文革十年》这样的惊世之作,其胸襟之坦荡,其笔锋之犀利,其目光之高远,在我心中激起了千层波浪。我为他们的精神所鼓励,再说也相信那种言者有罪、搞阴谋、“引蛇出洞”等不光明的作法,不会再出现了。我已活了80多岁,比起许多同辈们,已超额完成了“任务”,何来什么“后顾之忧”!
以后要写的,就是这三十多年来自己所想的、做的和亲眼看到的人和事,给后人留个真实的记录而已,别无他求。
解放初的日子真好过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市委招待所作所长。当时市委在重庆市区地势最高的枇杷山,招待所就设在下面的西南实业公司(现在的西南图书馆)里面,和市委组织部在同一个大院里。之所以要我到这里工作,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二野转业干部暂时住在这里等待分配,需要有人来管理。组织部的同志怕我有想法,特别说明待这批干部分配完成后,再把我调往其他部门。说实话,这工作比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时要轻松得多了,我去的时候,招待所的各项设备早已准备好,还有一个指导员,是个部队里下来的营级干部,叫张光泽,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尊重,服务人员大都是由脱险同志联络处转来的,大家都尽心尽力,工作干起来如鱼得水。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孩子不但有保育费,还有保姆费,当时曾流行一种说法: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就是地主了,那时候不但不讲节制生育,还学苏联鼓励女同志多生孩子,争当英雄妈妈,因此抚养孩子的这一切费用是不用操心的。至于我自己,吃的是团级干部才能享受的中灶,穿的是棉、呢军服,洗脸用具、内衣内裤都由上面发,每月还有四块银圆的零用钱,说起来不怕现在的年轻人笑话:拿着这些钱真不知道怎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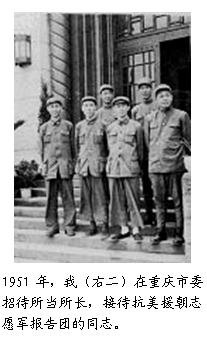
到招待所没几天,就在曙楼(原国民党市政府)召开本地和外来的党员干部会师大会,所有在重庆的地下党员都参加了,许多死里逃生的老战友在这里重逢,会场上一片喧嚷唏嘘之声。我在这里见到了曾经在江油一起工作的侯方岳,知道他后来由川北去了云南,然后作为“待解放区代表”去了解放区,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做准备。据我所知,他是待解放区到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的唯一代表。他抱着我高兴地说:“小林,这些年我多想你呀!”这边的话还没有说完,曾霖大哥又挤过来冲我高声大叫:“小林,听说你被捉去了,还活着呀?”特别是从华蓥山撤下来那些战友,有的握着手,有的抱着腰,跳呀、笑呀,个个都含着眼泪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是呀,国民党在最后崩溃时发疯似的捕人杀人,很难想象如果解放再延缓一月二月,甚至十天半月,我们还能在这个地方见面吗?
我在这里还与在川北地下时期的老战友李维、张文轩、王卜安、黄友凡、刘思安几个同志见了面。李维、张文轩到了延安后进入解放区,黄友凡于1948年也去了香港,他们都是随解放重庆的二野部队回来的。王卜安临解放作了江油中心县委书记;刘思安于1945年由成都回到万县后,一直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好在都活出来了,迎来了解放,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天会师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等首长都来了,原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也来了,讲话中除了欢庆解放,谈谈今后的任务外,特别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团结,还对外来干部作了更严格的要求:“搞不好团结,外来干部要负主要责任。”我们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也表示:“如果搞不好团结,主要责任在本地干部。”现在想起来,这显然是由于个人经历、成长环境、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分歧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初见端倪。有些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外来干部,以解放者自居,认为地下党的同志家庭出身复杂,立场观点模糊、政策水平低,成天和一些“社会渣滓”打交道,敌我不分;而一些地下党的干部,也认为那些外来干部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骄傲自满,看不起他们。不过那个时候,毕竟是刚刚解放,还没把这些事情上纲上线,大都做些解释调解和自我批评,然后一笑了之,平时里大家都和睦相待,好像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亲切而又温暖。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了领导并不觉得疏远,还要学学举手敬礼,我从未穿过军装,也不会敬礼,学起来时有点不伦不类,以后也就习惯了。那时候提倡体育运动,我还年轻,网球、篮球都是能手,经常被叫去陪领导打球。我去过范庄和枇杷山,与贺龙司令员和曹荻秋市长打过网球,还和陈锡联市长一起是市委篮球队的队员,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每逢星期天,原来在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总是这家走、那家串,借此机会打牙祭,谈谈所见所闻的新鲜事。遇到天气好时就约到郊外去转田坝子,最常去的有吴昌文、谢彬、吕迪等人,吴昌文有相机,照了不少照片,可是在历次运动中被丢失了。闲下来,大家就凑在一起吹牛。有个从军队来的同志说:“我们进军重庆时,路过南川白马寺,打了一大仗,又饥又渴的,看见桐子树上结的桐果,不认识是啥东西,有人说这大概是苹果吧?摘下来就吃,还没吃出个味道就吞进了肚子里,结果闹得又吐又泻。”
我说这有啥稀罕的?你们北方人没见过嘛。我没见过的事情,也出洋相。那天听说市委管理员发卫生费,好多人都有,就我没有。我找到管理员,去翻发生活用品的名册,上面真的没有我。我问管理员:“你怎么把我给漏掉了?”管理员板着个脸说:“你没有资格。”我一听说什么我没资格?我凭什么没资格?别人又凭什么有资格?现在解放了,大家都平等,你还欺负我,找你们的科长说理去!他还是板着个脸,理直气壮说好啊,我这就陪你去问陈市长,看你该不该得。
我一摔门走了,回到家里气冲冲的向宁君谈起这件事,她一听仰头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笨蛋,这是女人月经时买草纸用的卫生费,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此事让我落下了话柄,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见面就问我要不要领卫生费。
有些见过的事情,也会闹笑话。西南军区为任弼时同志开追悼会,也通知我去参加,坐位是在前五排,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宋任穷等首长。天气已经热了,礼堂里人又多,坐在旁边的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高兰戈叫我去把旁边柱子上的电扇打开。我虽然是城里人,对电扇也只是见过没有用过,但是已经被点了名,又不好说自己不会。我不懂装懂,上去东扳一下,西拧一下,急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浸湿了,电扇还是转不起来。正在开追悼会,不能乱说乱动,有的同志暗地捂着嘴巴,看我的笑话,好在还是有“见义勇为”的人,上来打开电扇替我解了围。后来有些同志笑我这个城里人,也是土包子。
外地的干部们很快分配完了,开始着手分配本地干部,组织部让我把解放前联系的一批干部造了名册,与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肖泽宽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张平河、田应泗、廖亚彬去了公安局,有的留在了市委机关,有的去市委党训班学习,连我从青年会带来的工人,都一一作了安排。起义后从岳池、武胜、合川撤下来的那些同志,有的留下来在重庆工作,有的坚持要回到家乡,也就为他们开了介绍信,转回当地。总的说来,当时的同志都很听话,工作分配进行得并不困难,可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说从合川下来的老陈。他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都较长,好像是1938年的老党员,起义失败后退到重庆,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策划渣滓洞的越狱,深入虎穴打探情报。可是这个人,就是骄傲,认为解放了就是自己的天下,老子枪林弹雨龙潭虎穴都闯过来了,未必谁还敢不给口饭吃?他这个老党员没弄明白: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不遵守这个原则,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会寸步难行。他不向组织报告,甚至连我这样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朋友也不说一声,就擅自离开重庆回合川,等我们知道消息,船都快开了。刘银州赶到朝天门码头去劝阻,他昂着个脑袋根本不听,还是一意孤行走了。可是他既没有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也没有工作关系的介绍信,合川的党组织无法安排他的工作,他又不愿意回头来找我们补关系,就这样一直悬着,成天发牢骚骂人。五七年,他被划成“右派”,不久愤然而死。
市委在枇杷山下设立了机关幼儿园,自然是全市的设备最好、师资最强的幼儿园了,市委干部的孩子几乎都在这里,民涛也被送进来全托。和陈作仪一起工作的彭咏梧,和他的妻子江竹筠都牺牲了,老彭的原配夫人谭幺姐初通文墨,本来可以去机关工作,可是为了老彭留下的两个孩子彭秉中和彭云,自愿到这里当保育员。炳中是幺姐亲生的,彭云是江竹筠生的,按规定他们是烈士家属,两个孩子的生活抚养费都由国家负责,但幺姐考虑到刚解放,国家还穷,只把彭云交给国家负担,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抚养炳中,后来她干脆把炳中送到条件大不如这里的保育院,自己专心带着彭云。因为彭云还小,谭幺姐就跟着去了小班。冬天重庆雾大阴湿,孩子的尿片不容易干,幺姐就把半干的尿片裹在自己身上,暖干后再给孩子垫上。因为这个原因,她得了风湿病,一直没有治好。幺姐带孩子们巴心巴肝的,家长们都很感激她,把她评为“先进保育员”。
宁君喜爱艺术,从孩子剧团出来后,没有能够和孩子剧团的战友们一起去延安进鲁艺学习,她遗憾了好多年。虽然后来也送她进了省艺专,却由于反对国民党强迫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被特务列上了黑名单,不得不半夜里翻窗子逃了出来。现在解放了,我们决定送她到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去学习,这是当时西南艺术界的最高学府,她多高兴啊!虽然她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有着在孩子剧团和中华剧艺社的实践经验,她满怀信心的想通过学习,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是好景不长,开学没两个月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先头还打算坚持,可是孕娠反应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受不了,只好含着眼泪退学了。她被安排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对象是市里各剧团,因为不坐办公室,经常下到各剧团了解情况,既有兴趣,又适应她有孕的身体。当时军队上曾有个规定,要具有“二八五团”资格的干部,才能够结婚。这个规定进城后改为“二八五营”,意思是年龄28岁、5年军籍、团级或营级干部,因此随军来的家属并不多。可就这样房子也紧张,我和宁君初先是各住一处,她调宣传部工作后总算找到了两间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窝。1951年的3月,宁君生下个女儿,正是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取了个赶时髦的名字叫抗美,诗伯从家乡找来她的侄女儿,当保姆。
别看宁君写的字像个初小三四年级的学生,可她说起话来有盐有味头头是道,又是从文艺团体中出来的,常常比她妈妈还气派,很多人都把她看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大学生。她为人又热情,与各剧团混得很熟,只要有名角演出的好戏,总能找几张前三排的戏票回来,让我和老战友们过足了戏瘾。宁君在解放前就常常进出舞厅,一解放就成了跳舞的积极分子,市委机关在胜利大厦组织的舞会,她是每场必到,那些有外宾参加的舞会,她都是当然的陪舞者。我虽然也爱去凑热闹,跳舞的水平实在是不及格,宁君从不愿与我共舞,我却死皮赖脸央求她做老师。音乐一起,我不是东拉西扯的不合拍,就是踩痛她的脚,往往是闹得不欢而散。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由诗伯最后收尾,安排完最后一个烈属,她去了市委党训班学习。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年轻的学员们很快都知道她是会打双枪的女英雄,纷纷要她作报告,听她讲述了当年在华蓥山战斗的故事,“双枪老太婆”的名声就此传开了。不久中央慰问团来到川北,慰问那些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英雄,名单中就有诗伯早年的名字“陈玉屏”,县里的同志们四处打听,才知道这个“陈玉屏”就是诗伯。岳池县派人来重庆,请她回家乡去当副县长,可是此时重庆市委已经决定派她去市妇联作生产福利部副部长,加上孩子们都在重庆,她还是决定留下了。
诗伯去的市妇联,聚集着好多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大姐,诗伯同她们开始相处得也不错。听说当年风风火火的陈大姐在共产党的政府里当了“部长”,早年女子实业社的那些姐妹和师傅们,还有些老关系也常常来找她。那段时间的诗伯,真是红透了半边天,成天乐颠颠的到处跑,她一上街就要碰到熟人,三天两天就要串起半边城。她本着组织妇女群众生产自救的原则,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好多个街道妇女合作社和烈军属合作社,自己亲自去联系业务,打手套,做衣服,还联系到好多军用制品,不但减轻政府救济的压力,还为国家生产了一些急用物品,受到各界的好评。“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了大游行,她动员了上千名街道妇女,手执鲜花国旗参加了游行队伍,这是解放后重庆妇女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游行,诗伯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供给制一结束,诗伯定下的级别就是16级,县团级待遇,每月工资106元,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却从来没有见到她主动缝制一件新衣,吃的也是食堂供应的素菜,可是来了客人,她经常是请客进馆子,过去结交的三朋四友来求助,她也总是大把大把的给钱,工资用完了就去借钱,总不能让别人空手而归。岳父牺牲后,她就开始吸烟,解放后有钱了,她还是像解放前一样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烟: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留着自己抽,好一点的华福牌香烟散给客人。她长期的肺病和气管炎老治不好,与她吸劣质的纸烟有很大的关系。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