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我和父亲去流浪
1935年的秋天,我和父亲开始了流浪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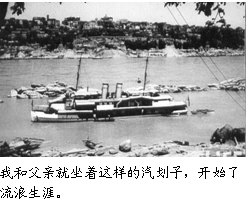
那天早上,唐家的管事拿着我们简单的行李,乘着一只小木船,把我们送到了民生公司一条汽划子上,驶往万县。
我是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汤溪河,进了长江。天啊,长江这样宽,这样大,江里的木船看上去就像漂流的树叶,岸边的人就像蚂蚁在蠕动,那些树啊房啊,随着江水直往后面跑,相比之下,家乡的汤溪简直就是条小河沟儿。那一年我十四岁,天性好奇,在船上东跑西看,转来转去,跑得累了转回来,才发现父亲站在船尾,沉默不语。
家乡云阳城远去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张飞庙也远去了,父亲望着滔滔江水,显得心事重重。我走到他面前,仰头问他:“爸爸,你在想什么?”
父亲说:“我想得多呢,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
我不甘心:“爸爸,你不是说要我做你的同志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这个同志说?”
父亲笑了,想了想问我:“那你说说看,我是不是‘疯儿’?”
“嗨,你想的是这个啊?我看只有七姑父和那些当官的才说你是‘疯儿’,老百姓都说你是好人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有一个好爸爸。”
父亲笑了,说:“我又多了一个知己的儿子。”
其实当时父亲的心境,是很凄苦的。十多年前,他失去了妻子,送走了老父,丢下我这个才三岁的独生儿子,也坐着这样的船,独自出门去闯天下。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才略有所成,就急忙回到家乡,想以一个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实现孙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想。这些年来,无论是独揽大权的团练局长,还是有职无权的国民讲习所长,甚至在监狱里,他都怀着一颗磊落之心,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他打土豪、除恶霸,悲天悯人,疾恶如仇,没想到到头来戴上了一顶“红帽儿”,两次坐监,几乎丢了性命。现在,家乡已经容不下他这样的“叛逆”,他只得带上唯一的儿子,再一次背井离乡,外出漂泊,内心的落寂之感,可想而知。而这些,确实是当时的我不大可能理解的。

长江上的险滩极多,常常打烂船,闹得船主们家破人亡,所以一路行船都很谨慎,虽然从云阳到万县只有180里水路,直到天黑掌灯时分,我们才到达万县杨家街口码头。我下了船,看见许多轿子赶来接客,万县的轿子做得极讲究,记得是用绿色的绸子做成的围子,看上去很是阔气,据说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我们因为有行李,父亲就叫了一乘轿子坐上,我跟在轿子后面走,到了旧城环城路上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家里。这家的主人姓兰,曾经与父亲一起在杨森的队伍里服役,官至中校参谋。后来刘湘赶走了杨森,驻扎在万县,他也就失业在家,靠着在军队里挣的几个钱坐吃山空。兰太太过去大手大脚地惯了,一旦过上了穷日子,就天天和兰参谋吵架,前不久干脆一卷铺盖卷回了娘家,兰参谋每天就在隔壁的小食店里吃豆花饭,每天的伙食费只要五角钱,剩下的时间,就约人在家里打麻将,每天可以得一元钱的“抽头”,也够他一天的生活了。兰参谋自己也打,他的麻将打得好,常常是赢的多,输的少。那段时间虽然潦倒,靠着当卖度日,可是毕竟还是官场出身,兰参谋依然保留着两套很体面的西装,出街的时候打扮得像一个很有钱的绅士,他说:“人是桩桩,全靠衣裳,越是倒霉就越要穿得伸展,要不然人家就更看不起你,找工作更是困难。”
兰参谋其实是一个有学问也有才干的军人,头脑也很清楚,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非常不满,也不愿意再去做他们的替死鬼,所以不愿意重入行伍;可是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再加上毕竟做过中校参谋,有些面子观念,高不成低不就的,正在为以后的出路苦闷,这些情绪都与父亲相合,两个人同病相怜,有摆不完的龙门阵。父亲给了他50块钱,作为我们父子俩的生活费,算起来省吃俭用,可以用上一个月。
当时四川有三个最大城市,除了成都重庆之外就是万县,它是从长江三峡进入四川的第一座大城市,下川东的门户,水陆交通都很方便,也是军阀混战的必争之地。万县市并不算大,人口还不足十万,因为是水陆码头,市场比较繁荣,最热闹的街道叫做二马路,来往做生意和下苦力的人多聚集于此;另外还有一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失意军人和政客,则多汇集在西山公园的茶馆内,他们大都打算在这里寻找机会,打通关节,寻得一官半职。父亲和兰参谋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万县的西山公园,是杨森驻扎在万县的时候修建的,号称川东第一园,又被称为长江边上第三园,其他的两园就是武汉的东湖公园和上海的虹桥公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东湖公园和虹桥公园我也都去过,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万县的这个西山公园。这里风景秀丽,奇花争艳,园内有广场,有球场,还有各种美味小吃,终日游人不断。园内矗立的那座钟鼓楼,有三十多米高,是城里的最高处,每到时辰,钟声响起,悠悠地在全城飘荡。就在这钟鼓楼内,有一块高十米、四人合抱的汉白玉石,被称为园内的第一景。它四面刻着公园筹建的经过,都是歌功颂德之辞,是杨森从五百里外的巫山运来的。当时没有铁路,川东地区崇山峻岭,交通极不方便,这样上万斤重的石头从山岩上打下来,又从五百里外的巫山经过水路和陆路运来万县,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父亲到万县后不久,就遇到了万县民众教育馆一个姓黄的馆长,据说也是云阳人。这个人为人正派,热心公益,在当地教育界很有些名气,对父亲在云阳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很欢迎父亲到他哪里去工作,愿意给一个馆员的名义,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总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又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父亲与我搬进了民教馆,黄馆长慕父亲之名,并没有真正分派他做具体的工作,父亲也乐得清闲,常常与他一起去拜访当年的老同学以及在杨森部队中的同僚,有时也去看看川戏,听听曲艺,还带着我去打网球。据我所知,这是父亲心情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时光,他又开始写起了打油诗,对象主要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可惜这些诗歌大多没有被记录保存下来。
有一天,父亲在街上碰到了他的两个同学,一个叫石克艰,时任忠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另一个叫唐隶华,在忠县保安大队任副大队长,他们是来万县参加第九区保安工作会议的。多年不见了,三个人一起去西山公园吃茶,各自谈了分别后的情况,父亲知道他们二人离开杨森的部队后,去成都通过武德学友会的关系,找到了省保安司令部的刘司令,得到了这两个好差事,掌握了枪杆子,负责地方治安,这在地方上算是了不起的大官了。父亲见机会来了,就向两个人谈起了我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照顾一下我的生活,并帮忙解决我的读书问题。石克艰非常爽快地说:“没问题,明天跟我一起回忠县,有得你的书读。”就这样,我跟着他去了忠县,父亲自己则去了重庆,找他的老上级雷忠厚雷旅长。
忠县离万县180里水路,沿途经过武陵、西界沱和著名女英雄秦良玉的家乡石宝寨。县城立在半山腰,有两个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贞节牌坊多。这里封建思想浓厚,一女不嫁二夫,丈夫死后要守寡一辈子,所以县城周围立有很多贞节牌坊。牌坊都立在大路旁,用石条砌成,还刻有很精美的花纹对联,当然这都是有钱有势有功名的大户人家的女人才有的“福份”。第二个特点,就是贫困人家的妇女,下苦力的多,而且一般都是到河边搬运货物,所以世人都知道忠县的妇女都是大脚板,缠脚的很少,虽然能够挣钱养家糊口,可是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很低,回到家里要生儿育女,洗衣做饭,还是免不了要受丈夫的虐待,只是比别地的女子更加苦累些。
我在忠县保安大队部住了几天,石大队长就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我已经与县中学的马校长说好了,你明天就去上学,读毕业班的寄读生,学费、伙食费我都给你交了,明年就能够毕业。”
石叔叔说的那个马校长,叫马仁安,是个大麻子,日本留学生,据说他在日本读了四年的书,每学期的成绩都是最后一名,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马八榜”,但是马校长办学很认真,请的教师也大都是名牌学校毕业的,在川东地区也很有名气。我读的第二十八班,是个毕业班,这又使我想起了在高小会考时得了个第二十八名,父亲为了安慰我,就和我开玩笑,说二十八合起来就是个“共”字,恐怕我将来要当共产党。当不当共产党我倒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我在这所学校读书倒是极认真的,虽然跟随父亲耽误了有些时日,各科的成绩依然能够跟上,而且作文成绩特别好,又喜欢运动,与同学们都合得来。加上我又是当官的介绍来的,所以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都很不错。我在家乡时,就爱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的小说,又半通不通地读了些父亲给我的《孙中山全集》和《新青年》杂志,到了这里,有同学借给我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上》两本书,在当时都是禁书,说是宣传共产党的。我便如获至宝,躲在被窝里看,越看越着迷,其中的许多词句,至今还背得出来。
这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了,回想起父亲的经历和自己的身世,再加上一些进步书籍的影响,想到自己也是个少年漂泊者,伤感和奋进互相交织,免不了思绪万千,便一口气写了一首200多行的长诗,取名《杜鹃声里》。这是我第一次写诗,七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春风吹拂着游子的心这时正是天街夜静杨柳儿披着绿衣低下了头杜鹃儿在树梢不断地鸣在一个静如死水的破屋里我殷勤地写着这一封信陪着我的是一盏惨绿色的孤灯和壁上映着的一条瘦长长的黑影还有杜鹃儿凄凉的歌声……中间还有一段:人说最伟大的是母爱我不让这话存在原来我的母亲早已经死去母爱从何而来……
结尾是:
要冲出牢笼,走向新的未来世界。
诗当然写得很幼稚,却也表现了一个少年的苦闷和要求进步的思想。我把它交给一个姓杨的国文老师,他看后大加赞扬,并写了“情意绵绵,思路开阔,文字清新,少年有为”十六个字的批语,还让我在班上朗读。很快,这首诗连同老师的批语,贴到了校园墙上优良作文专栏里,在全校引起了轰动,不少学生,包括一些女生拿着笔记本将它抄了去,从此我就成了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人物。
不过更使我得意的,是在全县运动会上大出风头。
在篮球和乒乓球的比赛中,我参加了校队,正因为如此,我们学校所向无敌,得了冠军。在田径比赛中,按照年龄我应该参加少年组,可是按照实力,我却参加了成人组,让全场的观众惊奇不已。比赛一开始,许多女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我的一边,为我鼓掌呐喊,我的劲头越来越大,在跳高、跳远、三级跳和撑杆跳四项中,都得到了第一名。这样的成绩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到后来简直就有点得意忘形,我带着这样的得意忘形参加了最后的一项跨栏比赛。本来我一直都跑在第一名,可是当我跨过了第七个栏杆的时候,禁不住回头往后面看了一眼,就在我还没有回过头来的那一瞬间,我摔倒了。我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前跑,可是已经有别的运动员追了上来,我只得了个第二名。
我当时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不少观众围过来,安慰我,鼓励我,我依然是伤心地哭个不停。这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由于骄傲自满跌的第一个跟头,虽然印象很深,却并没有接受教训,以至后来不断地再犯这样的毛病,吃了不少的苦头。
我的初恋
我的班主任杨老师,一直对我的印象很好,常常在各种场合夸奖我。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到他家里去玩,同去的还有几个女中的学生,杨老师一一为我介绍。其中一个叫杨光清的,是他的侄女,瘦瘦的,瓜子脸,以前我常常在篮球场上看见她,她跳得高,投篮也比较准,每投进了一个球,总是要笑一笑,脸上的两个酒窝特别好看。只要她一上场,周围的观众就要为她助威呐喊,我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却也情不自禁地为她拍手叫好。今天在杨老师家里看到她,真让我大为惊喜,虽然其他的女同学都在跟我说笑,说了不少的溢美之词,但是我只想听光清说话。光清说得不多,羞答答的,只是偷眼看我,可是一旦与我的眼神接触,就立即把头转了过去,到后来干脆跑进厨房,帮她婶娘做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杨师母有意的说:“光清这丫头一直清高得很,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有说有笑的,还来帮我做饭?”
光清嘟起嘴:“婶娘,高兴有什么不好?难道要哭才好?”
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会意地笑了。我装着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埋着头只是吃饭。杨光清一个劲地往大家碗里送菜,可是送得最多最好的还是我。饭后,杨光清和她的同学们要回学校去上晚自习,临走时专门从她叔叔的碗柜拿了一罐忠县的特产豆腐乳对我说:“我看你喜欢吃这个,拿到学校里去吃吧。”
杨老师留下我,又摆了一会儿龙门阵,有意无意地说起光清家里的情况。杨光清的父亲是北平朝阳大学毕业的,做过几年司法官,与杨老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一直都以兄弟相称。光清是家里的老大,很朴实,性情又活泼,喜欢打篮球,是女中的篮球队长。说到这些,杨老师突然问起我对光清的印象怎么样。我心里当然很喜欢她,可是又不便直说,只说是印象还好。杨老师趁热打铁,说光清对你的印象也很好,你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我冷不防被“将”了一军,支吾了一阵才说:“我还小,不好考虑这些事情。”杨老师笑笑:“没有关系,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的心事被杨老师点破了,从此常常想起光清,连晚上做梦也梦见与她在一起,梦见和她一起爬山,一起打篮球,还梦见寒假里她带着我一起回到她的家,她的父母都很喜欢我,弄了很多好吃的菜,其中还有野鸡野兔……
看来我已经初恋了。初恋真是甜蜜而又痛苦,弄得我寝食不安。我不想对杨老师说,更不敢给光清写信,因为忠县很封建,男女不同校,谁都不敢公开交往。终于有一天,我把我的心事告诉了父亲一个朋友的妻子李禾芳。李禾芳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在忠县的一个幼儿园工作,听我急急巴巴说完,就一拍巴掌,说她有办法,明天你到我这里来见她就是了。等我一转身,李禾芳就通过她在女中当老师的好朋友通知了光清。
没见面的时候想见面,总觉得见了面有很多的话要对光清说,可真的见了面,却又像哑了一样,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互相只是笑一笑,点点头。李禾芳见我们这样拘束,找了个借口转身走了,让我们俩单独呆在屋子里,我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东说南山西说海地扯起来。我们俩的话越说越多,也越说越随便,到后来我居然胆大包天,情不自禁地拉住了她的手,她也顺势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十五岁,还没有勇气拥抱和亲吻,不过我想我要是胆子再大一些,她也绝对不会拒绝我的。
后来我对自己的胆怯非常后悔,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
忠县邮政局的局长叫郑祖骏,一家三兄弟都擅长打网球,号称独霸四川网坛的郑氏三杰。郑家老二叫郑祖湘,曾经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某大学当教授;郑家老幺叫郑祖驹,他的球艺最好,长期在成都陪一些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太太打球。在一次全国性的网球比赛中,老大祖骏和老幺祖驹都成为四川队的代表。
郑祖骏几乎天天都要去公园打网球,刚好网球场就在保安大队的旁边,副大队长唐隶华也喜欢打网球,只要郑祖骏一来,他就要去球场,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也要跟着去。那个时候忠县的网球运动才刚刚开始,前去打球的大半都还是初学,只有教堂里一个姓刘的牧师,和县中学一个姓陈的美术老师能够与郑祖骏打上几手,令这个找不着对手的名将大为苦恼。就在这个时候,我上场了,他见我小小年纪,不慌不忙,不惊不诧,在接发球、抽球和拦网方面都显得很熟练,不禁喜出望外,以后就经常让我去陪他打球。我拜他做老师,他也乐意教我很多打球的基本技巧。后来学校放了寒假,他干脆让我住在邮政局里,打球的时候也方便。
我在邮政局里,除了打球,还能够看到很多的报刊杂志。我特别喜欢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金仲华主编的《永生》等,这都是些进步刊物,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安内攘外”的政策,争取民主自由等等,常常议论时事,在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令我非常着迷,只要杂志一到,我每篇文章都要读完,每次都有很多的感受。正是这些文章,对我后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久,我接到了父亲给我的信,说他又回到了万县,还告诉我说万县专署很快要办一个地方建设干部训练班,训练各县保送来的教师。他已经找好了关系,让我去参加训练,毕业以后就可以当教师有工作了。这对于漂泊中的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郑祖骏夫妇和石、唐两位叔叔,同时也告诉了县中的杨老师和平时要好的几个同学,大家在为我高兴的同时,都有些难分难舍。郑祖骏送了我两把球拍和十多筒球,两个叔叔还给了我一些钱,杨老师夫妇一定要给我饯行,并请来了杨光清作陪。杨老师夫妇都知道我与光清的关系进展很顺利,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也表示以后要多写信,并希望光清女中毕业后考到万县的省立师范学校去读书,争取今后在一起工作。那天光清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后来趁着她的婶娘不注意,悄悄塞给我一个特别的信封,匆匆地说了一句:“拿回家去看。”
我哪里等得到回家,一离开杨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两张雪白的手帕,一张绣着两只鸳鸯,另外的一张绣着“花好月圆”四个字;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运动服,手里抱着个篮球,朝气勃勃,英姿飒飒。最重要的,是一张西式的信纸,上面用娟秀的笔迹写了短短的几句话:
青哥:恨相见太晚,但愿一个美丽的梦最终会变成现实。你走时我不来送你了,请原谅。清妹
第一封信,就这样称兄道妹,而且弥漫着伤感的情绪,显然她已经对于我们的初恋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是我沉醉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中,也为很快又要与父亲的团聚而兴高采烈,当时并没有体会到她的这种情绪,只是急急忙忙地准备行装,和应付许多意外发生的事情。离开忠县的前一天,我在郑祖骏家刚刚吃过午饭,就不断有人送信来。送信的都是女中的校工,为了表示礼貌,同时也是因为高兴,唐隶华每次都给送信者一块银元作为酬劳,当时的一个银元可以兑换六串铜板,能买好多东西,这样的酬谢应该是很重的了,不料到后来送信的越来越多,一连送来了二十多封,令唐叔叔大为破费。这些信除了一封是老师写的,全都出自于女中学生的手笔,其中只有少数几个是在杨老师家里吃饭的时候认识的,其他的都在信中自我介绍,有的是县党部和县政府官员的女儿,有的是男女中学老师们的妹妹或者是亲戚,有的说是在运动场上认识我的,但是我自己却没有什么印象。信中大多是称赞我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也有的羡慕我的文才,还有的夸我的人品好,长相也好,要想与我结成兄妹。还有的露骨地说我是她最理想的对象,希望能够与我交个朋友。还有一封信,干脆地表示希望我能够成为她终身的伴侣,还随信附上了她本人的照片和亲手绣的手帕……
为我送行的朋友们陆续的都来了,唐隶华叔叔却不顾我的情面,把所有的信都一一拆开并当众念出来,一边念一边哈哈地笑着,然后把它们都挂在一根绳子上,说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叫我闭上眼睛,摸到谁的信就是和谁有缘份。我羞得满脸通红,只是往后躲,可是大家不依不饶,郑太太用一根手绢蒙上我的眼睛,硬把我推到挂信的绳子跟前。我被逼得无路可走,一伸手抓下三封信来,大家又哄闹起来,说怎么能够一把抓住三个不放?看不出来啊,你的心也太大了嘛,那不是对爱情不专一吗?
我挣开他们,跑出了屋子,站在外面只是喘气。阿弥陀佛,看来他们谁都不知道我真正的秘密!
忠县,长江边上一个偏僻的小城,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那里有多少值得我怀念的故事。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