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方
4、南长街院子里走出来的新派学生
陈家、方家虽然住在四合院里,可是不受老规矩的限制。
先说说这个家族的女性。
陈家六个女儿,我外婆和三姨婆是没有上过洋学堂的。我外婆因为是头胎,太外婆生她时只有17岁,而且那时也没什么新学堂可上,因此可能在教育方面有所欠缺。但太外公和太外婆是亲自教女儿们的,女儿们跟母亲学过《诗经》、《唐诗选》等,而不是学什么《女儿经》。因此,我外婆的中文水平是可以读四大名著,还会画些国画的。
我二姨婆是靠自己的挣扎和她的三舅庄蕴宽的栽培,最后去了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硕士、女教授,著作颇丰。
方家三个女儿,我大姨是女孩儿中的老大,外公也是新思想,所以自然把她送到新式学堂上学喽。
我大姨比我六姨婆小不了一岁,刚到南长街时,她俩是在女高师附属小学上学,虽是两辈人,但是是同学,更是好朋友,她们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同班同学浦熙修。
附属小学是在西城东铁匠胡同,因此学校又叫东铁匠胡同小学。因为大姨和六姨婆住南长街,浦熙修住西长安街六部口,大家同路,因此三个好朋友放学时总是同行,路上每人买一根酱萝卜、买一把铁蚕豆,都能吃出各种花样来,能乐呵一路。大姨和六姨婆常去浦熙修家玩儿。浦熙修也常来南长街,她还向我太外婆学习画画,她画的藤萝很有我太外婆的画风。
放假时三人又一起出去旅游。
有一年暑假,三个好朋友一同到香山我们家一位亲戚的别墅那里住了一周,在那里她们见到林徽因坐轿子下山。六姨婆后来写了一篇小文,说因那惊鸿一瞥,她认定林徽因是她“今生今世见过的第一美人”,并且很准确地说出林徽因的美其实更多来自“内心和骨头缝里透出的智慧和书香气”。

我六姨婆发表在今晚报上的文章《我见过的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这里他说的“徐志摩和我两个姐姐姐夫都有交往”,指的是二姨婆陈衡哲和任鸿隽、四姨婆陈衡粹和余上沅。据我六姨婆的儿媳告,她们那天见到林徽因是和陈省身一起上山的。六姨婆和我大姨的这段回忆略有不同,可能是年头长了,记忆不够准确

林徽因
那是她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天下毋如读书乐!”(东铁匠胡同小学校歌)
后来大姨跟浦熙修又在京华美术学校同学过一段时间。
解放初期浦熙修到北京工作了,六姨婆专程从天津来北京探望,那天是大姨和六姨婆一起去浦熙修和罗隆基在灯市口的住处看望她的,可惜后来……。
我爸也认识浦熙修,那应该是40年代的事了。
而罗隆基的第一任妻子王右家曾经是我四姨婆的同学。

我大姨(右)、浦熙修
我大姨和我六姨婆上女附中时,五、六姨婆已经在女附中上学了。那时的女附中在辟才胡同。
我竟然在1936年的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中找到了女师大附中的位置,还有皮库胡同。
我表姐贺凯芬说:当年她母亲(我大姨)和六姨婆走路去辟才胡同上学时要穿过皮库胡同,从东口进去,从西口出来,每逢进皮库胡同时,她们就会喊“穿皮裤子喽!”皮库胡同弯弯曲曲的,她们拐了两个弯儿,要出胡同口时又会喊“脱皮裤子喽!”然后她们就进入南北走向的二龙路,沿二龙路向北走,就进了女附中在二龙路的南门,现在那里是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北校区。
以前从女附中南门进去有个红楼,红楼和女附中在辟才胡同的北门之间有一条曲折的长廊,像颐和园长廊那样带顶棚的,可漂亮了,可惜后来都拆没了。

1936年的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方框内为女师大附中,那条线就是皮库胡同
那时的女附中入学考试严格,我大姨在那一届考了第四名,但是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萧友梅的妹妹因为头发过短,不符合学校要求,没被录取,于是我大姨上升为第三名。
学校校风极严,学生都穿黑裙子、白袜子,头发分成两边,编成小辫,再盘成两个‘粑粑头’,贴在两耳朵处。学生循规蹈矩、不苟言笑,学习很努力,学校的老师都是名师,还有北大、师大等名校老师自动来兼课。
但是有着这些盘辫子照片的学籍卡后来竟然被销毁了。我一位表姐说,1952年,她刚上师大女附中没多久,就被叫到辟才胡同校区去,在南门口地上堆着一大堆很讲究的学藉卡,每张的上方都贴着一张不小于3吋的照片,下方是学生信息,照片上的女学生有些是梳着两“盘头”的,也有梳两条长辮子的。学校交代她们把这些学籍卡都烧掉,这些年轻的面容对着她,使她不忍销毁,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学校的命令,于是这些记载着这座城市、这所名校一部分历史的卡片就变成了一堆灰烬。

20年代女附中毕业生合照
四姨婆是1920年从苏州振华女中转学到北京的女师大附中二年级的,当时还叫女高师附中。在这里学习了三年,1922年高中毕业后,她考取了北京艺专西洋画系,但是学校收费很高,后来她看到女高师(即后来的女师大)招生广告,不收学杂费,还供食宿,于是她放弃绘画爱好,去投考女高师,当时学校只招40个学生,四姨婆在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上了国文系。
四姨婆的授课老师有鲁迅(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伊默、马裕藻等名师。鲁迅先生教她们《中国小说史》,四姨婆对先生思想的深邃、讲课的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印象深刻。她说:“先生讲课,从不是就书本说书本,总是在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启发学生通过文学作品或资料,展开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她还记得先生讲课时的话锋如同他的笔锋一样犀利,有一次,鲁迅讲到保皇派康有为主张对皇帝跪拜,康有为说“否则,要膝何用?”先生反诘问道:“那么岂不是可以引伸为头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吗?”
四姨婆和她的同学与先生熟悉后,还常常结伙去先生家串门,亲眼看到先生对他母亲的孝顺,同学带来的糖,他也要“捧些给老人吃,有时说些笑话,逗母亲开颜一笑。”她说鲁迅先生绝不是一个冰冷冷的斗士,他是很随和的人,她们于是也大胆随意,甚至还对鲁迅先生乱蓬蓬的头发、长长的胡子和不考究的衣服提出疑问……。

鲁迅
四姨婆对“三一八惨案印象深刻,她说,1926年3月25日,全校为死难同学开追悼会,鲁迅先生一早就来到学校,沉思、徘徊于大礼堂外,满腔怒火,只觉得光天化日之下,经历实“非人间”,那篇著名的 《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便是在这天写成。
四姨婆一辈子教书育人,她说从鲁迅先生身上学到了他尊重青年、爱护青年的思想,也学到很多有益的教学方式,那就是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以上关于鲁迅部分来自陈衡粹《回忆鲁迅先生几件事》。

陈衡粹,《回忆鲁迅先生几件事》
在女师大(她上学第二年就改名女师大)上学期间,四姨婆除了听课,还广泛地参与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活动。那时女师大公演王尔德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她在其中饰演男主角,因为那时还不兴男女同台演戏 。那天四姨婆在台上演戏,我大姨在台下当观众。为了演男人,四姨婆戴了一顶帽子遮住头发。戏中有一个情节是男主角往沙发上一仰,结果我四姨婆往后仰时帽子掉了,一头长发散了下来……。

话剧《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海报
四姨婆还常常去六国饭店跳舞、出入东单一带洋行、参加教会活动等。她也去欧美同学会,有时还带我大姨一起去。
欧美同学会本来是私人的,是胡适、任鸿隽、我二姨婆陈衡哲他们创立的,在南池子的房产也是他们集资买下的,至今,南池子欧美同学会的入门处还可以看到这些创立者的合影和名字。

现在的欧美同学会大门口
有一次在欧美同学会的集会上,我大姨见到了胡适和他的夫人江冬秀,我大姨形容说:“她同胡适一起进来,她一身大红缎子花棉袄,大摇大摆的,怀里还抱着个暖水袋;然后大模大样坐下,双腿撇开;一张口就是一口苏北话,特俗。”
大姨形容胡适个子高高的、白白的,非常文雅,典型的白面书生。当然这是一个十几岁女孩儿的直观感觉,她说不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评论来。她只是心想,这么文雅的胡适之怎么会娶了这么一位俗气的老婆?觉得二人不相配。

胡适和江冬秀
四姨婆和一些新派青年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学习国外的新花样,比如她们学会了当时国外时兴的用丝线和小梭子打的一种花边,非常好看,法文里叫做 Frivole 的,说明此织法可能起源于法国。那是教堂传授的技艺之一。改革开放后,国内大量出口国外的昂贵的纯手工沙发蓋布、窗帘桌布等都是基于这种技法。我表姐多芬留学苏联时还曾在莫斯科买到过教此法的小册子。

随便找了张图配
除了我二姨婆,我四姨婆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领跑人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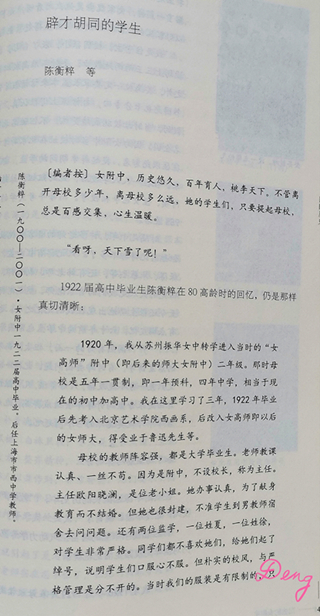
《远去的女附中》中我四姨婆陈衡粹的文章
五姨婆长得漂亮,有着中国古典美女的美。她在家里是公主,太外公喜欢,哥哥们也宠她,为这个还引起六姨婆的妒忌呢,她说,哥哥们都喜欢她五姐,他们出去到公园儿玩儿,只带五姐,不带她去。
在学校五姨婆是校花,不但漂亮,而且功课好,所有科目的成绩总是第一,无论是书法,还是昆曲、吹笛、吹萧……,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学校组织的文娱活动都会有她的表演:歌唱,独舞。纱裙、长辫、蝴蝶结,令人眼花缭乱。

陈戊双就是我五姨婆
她在女附中时主演过《葡萄仙子》,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她穿着纱裙在舞台上跳舞,纱裙前面斜着绣了一大串葡萄。漂亮极了。葡萄仙子有台词说:‘我要发芽,长叶子,然后开花,结果……’;之后就有甲壳虫、益虫上台表演……。”
别的节目中,“她穿着长长的纱裙,裙上缀着亮晶晶的闪片,两条乌黑的长辫一直拖到膝盖,辫梢系着大大的花蝴蝶结…转起来的时候,蝴蝶就随着辫子飞舞,裙子上小星星、小月亮熠熠发光。”(大姨口述)

五姨婆旧照
六姨婆是个大大咧咧的人,父母不怎么宠她,按我大姨的说法就是“没人管”,这也养成她特立独行的性格。
她也是女附中的佼佼者,她和四姨婆都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1926年3月25日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开追悼会,六姨婆作为校派代表参加。六姨婆后来是南开大学教授。下面是我六姨婆在《远去的女附中》中的文章及照片。照片中的陶强是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的夫人,下面我会讲到她们的故事。
六姨婆也喜欢昆曲,她后来在南开大学还组织了一个“甲子曲社”,不过这是后话。

《远去的女附中》中我六姨婆的文章及照片
那时四、五、六姨婆和我大姨,经常看外国电影,那里面的许多外国歌曲他们马上就学会了,平时都是用英文哼唱的。
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新派青年。
后来,我大姨的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也都从女附中毕业,可以说这家族四代人都与女附中有深厚感情,不过这又扯远了。

1924年北京女高师附中篮球比赛,女高师附中就是后来的女附中
不能光说这个家族的女性新派学生,也得讲讲男孩子。
我外公在广东曾经办教育,所以他懂得怎么教育孩子。从苏州到北京后,经我外公的补习,我大舅1920年考入了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中学,即现在的北京31中。崇德中学在西城绒线胡同西头路北。学校只有一栋三层的楼房,东边一个大门进去,第二层有七八间房子是中学的教室,西边从另一个门进去,是小学部的教室。
大舅还记得当时校长的名字叫Thomas Scott。此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1908年来华传教,1913-1920年任崇德中学校长。
我的二舅公陈益(字谦受)当时在这个学校的小学部上学,比我大舅低三个年级。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足球队,长期训练,锻炼出几名足球健儿,并且曾与东交民巷英国驻军的足球队比赛。我二舅公也参加了那个足球队,他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经济系。

建于1916年的崇德中学老校门
我大舅因为刚从苏州过来开始有些跟不上,但不久之后就名列前茅。校长表扬他,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英文成语:slow and steady, always win the game(稳扎稳打,必操胜券)。
大舅的数学得益于一位英国教师,是一位未婚的老小姐,中文名字叫卫淑祎,教《代数入门》和《高等代数》,讲的清楚、耐心,为我大舅后来的学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一位英国老太太教授西洋史,也有洋人教的理化课。
教中文的老师都是什么举人秀才之类,也教的很认真,每天学《四书》、《左传》等。
我的小姨夫许京骐后来(30年代)也是崇德中学毕业的,也就是说亲戚中至少三人上过这所中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三十一中校门
大舅在崇德中学读了三年,学校改制,他就不再读了,1923年考入了唐山(交通)大学预科二年。唐山(交通)大学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老师一律用英文讲课。大舅上了一年预科,升入本科一年级。他实际上只上了4年中学。

唐山交通大学老照片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